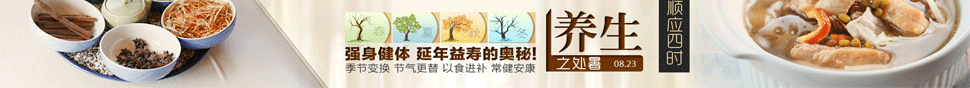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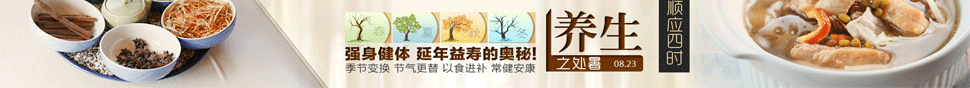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年春天的一天早上,我正在家里,忽然间听到外面一阵排山倒海的倒塌声。我冲到门口一看,原来我家对面的一排店铺全倒了。房子倒后冒出的灰烟向四处扩散。房主们站在街上,讲述着房子倒塌时的情形。
这一排房子,共有四间店面,从右往左数, 间是霞浦老四师傅的做篾店,第二间是马记枕头店,第三和第四间分别是理发店和打铁店。这天早上,房子要倒以前,房子里发出了很大的叽叽嗄嗄的响声,起先,大家并不在意。后来,声音越来越大,四家人都不约而同地跑到街上来,想相互问个究竟,谁知刚跑到街上,房子就一声巨响,全倒了。还好这四家店铺,家眷都不在里面住,老板师傅逃出来,就等于全家都出来了,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下尾街的店铺,都是这样,排连排,间连间的。几百年的老铺了,有的东歪西斜的,说倒就倒,而且倒下的是一整溜。
下尾街的街市,与宁德县城其他街巷不同,这里汇聚了手艺人、生意人、在海里讨生活的人、江湖人,以及附生于这些人的人。这里寸土寸金,人们只要能挤得一小块地方,就能够养家糊口,过上温饱日子。
听祖辈的人讲,下尾街是宁德县的城外街,它直通东城门。反过来讲,从东城门出来,过了一座桥(金鳌桥),就是下尾街。下尾街属金鳌境,解放初期,金鳌境被一家保险公司占用,保险公司撤了以后,就成了县供销社的地盘了。
下尾街的开发,最早要追溯到明朝。当时的陈、林、蔡、郑等姓,靠着海上的优势,发财了。他们在城东的海边建起了大房子。傍着房子,也建起了一间间的店铺。后来生意越来越兴隆,市面也越来越扩大,在南面也有人也盖起了店铺,这样,经过几百年的演变,就形成了后来的下尾街。南面的店铺没有大厝的依伴,没有街北面房高大、美观。人们不敢盖得高大,一怕东湖塘海水的侵袭,二怕台风光顾。直到六十年代,东湖塘围成后,有些房子才敢向东面的海边再扩展,形成了后来完整的下尾街。我家就在水楻头我家住的地方,确切地讲,是下尾街的水楻头。为什么叫“水楻头”,老人说,这是因为很久以前,从城东门出去,去五都下(泛指兰田、马山、汤湾一带),要走过一条大沟壑,这条大沟壑经长年日复一日的淡水和海水的冲击,海泥成了象圆楻一样的形状,久而久之,人们就把这地方叫“水楻头”。后来有了下尾街,还叫这地方“水楻头”。
很多人只知道这地方叫“水楻头”,而不知道“水楻头”怎么写。到了年的秋季,我们家对面搬来了一位“法师僧先生”,他开了测字择日馆,他在店铺门前的墙上,写了大大的“水楻头”三个黑色大字。不知是这位“法师僧先生”的招牌的效力,还是他的真本事,择日馆的生意很兴隆。那时,“去水楻头法师僧店讨日子”,是许多宁德人口头话。篾料店与“去路”我家开的是一间篾料店,说是篾料,其实也有木桶,也有卖木板料的,还有铁制的大锅、小锅。
每天的上午,是我们家最繁忙的时候。我奶奶、母亲四点多就起来煮饭,五点多,全家人吃罢早饭,各就各位。我父亲开店门,摆设店面。这时,就有乡下人挑着萝、篮、木板到店送购。验货,讨价还价,购买,都是我父亲的事。我哥哥则负责“去路”——到乡下人进城必经的几个路口,截买我们店里需要的货物。
有时,会因为当季货物奇缺,几个店铺的“去路”人会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去截货。这样,城西面最远会走到石后、洋中;南面则走到罗源、中房等地。
“去路”的人碰到自己所需货物时,与货主谈妥价钱,写张条子,说明货名、数量和单价,交货主连货送到你的店铺。中途如果有人抬价、或要分买,货主都不会答应,你只管放心。有时,遇到特别熟悉的货主,你可以连条子都不用写,货主会自报路上讲妥的价格结账,买卖双方都十分满意。
我家开篾料店的时候,我才七、八岁,即便这么小,也不能闲着。奶奶会拿一张小凳子,叫我坐在店门口,帮助看店。我家店铺里也有自己做的东西卖,象锅箲、竹笆子之类,这是我母亲和姐姐做的。她们家务后,就坐在店铺的一侧加工这些东西。到了公私合营时,我父亲进了供销合作社后,我家才把店铺租人开油漆店。但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们仍然在做手工竹器,在自家的大门口,摆个小摊卖。图为宁德蕉城区石后乡芹后村的老篾匠李伏清,如今这门手艺已经难有传人了在下尾街,沿街有店面的,和我们家一样,从早忙到晚;没有店面的,也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,或者操劳各种工艺,赚钱营生。整条下尾街,从大人到小孩,几乎没有一个闲人。补牙刷店在法师僧择日馆的隔壁,是补牙刷店。过去的人节约,衣服、鞋子破了,有补的,牙刷用脱毛了,也有补的。这是当时宁德 一家补牙刷店。店面还很大,有雇几个学徒在帮忙。店的上面吊了一个大架子,架子上排满了新做的、已经补好的和没有补过的旧牙刷。补牙刷的毛用的是猪毛。他们家的后面是宰猪场,他家的孩子要早起,到猪场捡猪毛。迟了,屠夫门会把猪毛混着其他杂物扫到溪里。猪毛拿来后,要一根一根挑捡,专捡那些长的、粗的。达到一定数量后,要放在锅里煮,直到硬梆梆的毛变软了,才能捞起晾干备用。牙刷的主杆是用一种红硬木或者竹子做的。在主杆的一端用刀划出四道横线,再钻上小洞,将一小撮一小撮猪毛象纳鞋底一样,牢牢绑在小洞里。半天工夫,做不了三、五把牙刷。那时,一把新牙刷卖三分钱,相当于当时一根半油条的价钱。补一把牙刷,也只有1分钱到2分钱。补牙刷的生意很红火,他们一家从早忙到晚。民国老牙刷“灯笼两头空”下尾街共有三家灯笼店。灯笼是宁德人红白喜事必备的东西,需求量大。扎一个灯笼,要经过二十八道工序。这二十八道工序又主要分成两个阶段。 个阶段,是做灯壳,技术性很强,细心和灵巧是基本要求,都是妇女在做。要把做灯壳的一整套技术学到手,要经过很长时间。一般都是媳妇跟着婆婆学,一代传一代。第二个阶段就是糊灯,工序很多,靠得是耐力,男、女都有干。有的店,遇到年节,或者是订货扎堆时,往往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。
我有个婶婆,我七、八岁的时候,就看到她在编灯壳。婶婆的这套技术却是从她娘家带来的。原来,从我父亲那一辈往上数,我爷爷的爷爷的家道是富有的。他们靠做糖、酿酒、贩茶叶、跑海运赚了钱,就在东门外盖了很多房子,又依着大房子边盖了很多店面,家境越来越发达。听我母亲讲,最炫耀的时候,全家人分配收租都来不及。无奈后来不少人染上了鸦片,家道就慢慢地衰败了。
我这个婶婆的娘家也不富有,她母亲靠编灯笼贴补家用。她嫁到我们这个家族,原想可以享福,那知到老时,也要操起娘家的手艺。婶婆生有七、八个孩子,叔公死的早,她没日没夜地编灯笼,常常是明天早上煮饭的米,要等着今天晚上的灯笼编出来卖了钱,才能解决。劳动的人身体硬朗,婶婆直到改革开放的第二年,年,96岁才离世。传统灯笼工艺如今也是传承乏力了灯笼分类型很多:有宫灯、有庙灯、有喜灯、有天灯等等。虽然做灯笼的在下尾街只有可数的几家,需要用灯笼的却是全县,仍至霞浦、罗源、连江等邻县的千家万户,但是下尾街却有一句老话,叫“灯笼两头空”,意思是说,做灯笼的不会发财,至少不会发大财。
做手艺的人不会发财,这是下尾街人的共识。
那么,做金、银手艺的人又怎样呢?打金和打银下尾街做金、银手艺的人很多。金店、银店,人们习惯上叫打金店、打银店,还有打铜店、打锡店、打铁店,这些店铺加起来,少说也有十几、二十家。他们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,只传内,不传外。那时的金、银首饰都是手工制作,工具特别多,有一个拉金线、银条的架子。经过这个架子拉出来的金线、银条很细、很匀,可以用头发丝来形容。拉出来的这些线,就是做首饰的最基本的元素。还有炉子、锯子、钳子等等。
这些店铺的一家子,也是从早忙到晚。那时候打银、打锡器的人比较多。打银是小孩满月、周岁用,打锡器的则是家里有姑娘出嫁做嫁妆用。来的顾客也是平民百姓居多。这些银、锡器价格便宜,大家买得起,可想而知,手艺人赚到手的钱肯定是不会多的。挑水夫和宁德最早的自来水厂最让下尾街人纠结的,要算吃水了。
下尾街是在海滩上造起来的街,全街人的吃水,都要到城内去挑。生意人、手艺人那有时间去挑水,于是就有人干起了挑水的行当。我知道的,最早的一担水是2分钱,后来就1角钱三担,再后来5分钱一担,到了六十年代后期,涨到1角、2角钱一担。
街上有一个叫“琴姨”的妇女,40多岁,专门挑水卖,我家的水都是她给包了。
“琴姨”有一段悲惨的经历:年,粮食最困难时期,她的两个十五、六岁的男孩,到山上采了很多漂亮的野菇,拿回家煮了吃。孩子吃得多,“琴姨”和她老公只吃一点就忙事情去了。没有多久,她的二孩子大叫肚子痛,在地上打滚,老大看着没办法,医院,医院,老大的肚子也痛了,没有多长时间,两个孩子都相继死去。两大人吃得少,只是肚子痛一下就好了。
这件事对“琴姨”夫妻打击很大,他们只有这两个孩子。只一夜工夫,“琴姨”的头发全白了,人也苍老了很多。从那以后,她就很少与别人讲话。仍继续挑水,挑来的水倒进人家的水缸里,收了钱,头低低地走了。民国挑水夫年,下尾街也有过自来水。有一个叫“细孙”的,叫了几个人合股,办起了自来水厂。这可是宁德县最早的自来水厂了。
源头是溪流坑的一股清泉水。他们把这股水用毛竹管接到下尾街。要用自来水的户也要出一笔钱,就把水接到你家。没有龙头,是小竹管套上大竹管当龙头,不用水时,就用一段小木头塞进小竹管口,把水堵住。
毛竹水管是沿街面接过来,它经不住街上过往东西的碰撞,经常破裂,使竹管经常漏水。我看他们几个人整天忙碌,这里补漏,那边堵口。后来,他们就把水管埋到地下去了。一段时间后,水漏了,在地下,看不见,他们又这里挖挖,那里挖挖,好不辛苦。没过多久,水厂就倒闭了。
电厂、广播站、春晚与洋油灯下尾街有路灯,那是在年初。
那时候,有人在东门兜办了个电厂(现在邮电大楼),是柴油发电。电厂的大门进去,是一个大水池,发电机就放在水池的后面。机器工作时,发出很大声响。东门兜一带的路灯就是这个电厂送电的。下尾街离东门兜很近,又是集市重地,也接上了路灯。电厂有两个电工,一个叫“人干”、一个叫“细弟沙”(“沙”是宁德人对某种手艺精通的人的尊称),细弟沙是福州人。那个电厂,只有他们两电工,安装电灯,维护线路,都是他们的事。
我家离电厂很近,两个电工师傅又都是住在下尾街,我们很熟悉,所以我经常去电厂玩。
后来,电厂的楼上办起了广播站。年春节除夕,楼上的广播站很热闹,很多大人拿着二胡、手风琴等在吹拉弹唱,曲声和歌声传到对面街一根电杆的大喇叭上,大喇叭传出的歌曲声很响亮。用现在的话说,这可是宁德县最早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了。
街上有路灯,但是家里点的还是 灯。
我奶奶说,最早这 灯也不叫 灯,而是叫洋油灯,它是跟洋火、洋油、洋钉等一起从海上进来的。没有这洋油灯以前,下尾街人家晚上都是点“灯盏”。“灯盏”我见过,我们家店铺以前有卖。它是一个竹架子,架子上放着一个很小的铁锅,铁锅里放着菜油,一根“灯芯”泡在油里,只露出一段小小的头在锅沿上,点着这锅沿的“灯头”,就是一盏照明的灯了。要不时挑芯头,并把烧残的灯芯去掉,要不,灯会很快熄灭。每天晚上,加班的人有,娱乐的人也有。我家地方比较宽敞,街坊们有时也会聚集在我家打牌。主要是妇女打四色牌。她们一般都是晚上八点多开始玩,十一点就散场,谁有空,谁参加,所以每晚玩牌的人也不完全一样。父辈们也有玩麻将的,他们玩的地方很隐敝,从不让小孩子知道。我只是偶尔在白天听他们谈话中,有讲到晚上麻将的事才知道的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玩纸牌、打麻将是不可思议的事,如果被人发现,是要被当成坏分子处理的,轻则要罚扫街,重则是要监禁。夏夜的“没脚竹床”下尾街夏天的晚上,又有一番情景。
下尾街的房子。特别是街东边的那一排排紧紧贴在一起的木板房,大都是一层再加一个矮矮的阁楼,做手艺、做生意的人,工具杂物特多,差不多要占去半个屋子,还要扣除店面,剩下居住的地方就不多了。冬天还可以将就着过,到了夏天,屋子闷热得象火炉,实在是呆不了人。而且,每家大都是三代、四代同堂,少说一般一家也有六、七个人。空间那么小,那么热,人又那么多,那夏天怎么过呢?
有办法,我们每家都备有很多简易竹床,没有安装四只脚的,放置方便,什么地方都可以放。一到傍晚,吃罢晚饭,下尾街人就拿着竹床到外面占位置。离水楻头不远有一个大市场,那是我们放“没脚竹床” 的选择。在这里,有人讲书,讲故事,讲宁德新闻,这些我们都很爱听,躺在竹床上,听着听着,就进入了梦乡。也有人嫌嘈杂,蚊子多,他们就把竹床放远一些,放到现在的东门商场那里,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坪地,晚上很宁静,蚊子也比市场少,也是适合睡觉的好地方。下尾街上有一间打铁铺,在街的东边,铺面不大,大概只有十多平方米。店铺上面也是一个小阁楼。店的中间放一个烧铁的大炉子。那炉火从早上一直烧到晚上。夏天,天上的太阳晒,屋里的炉火烤,这店里热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店老板,下尾街人都叫他“打铁师傅”,那时已经60多岁了,不抡锤子了。店里的活由他儿子在打理。原来干重体力活的人,一旦停歇,加上吃得讲究,人就会一下子发胖起来。“打铁师傅”就是这样,没几年,人就胖得连路都走不动了。胖的人睡眠好。
“打铁师傅”每天傍晚早早地就拎着一架“没脚竹床”,找一个好位置,躺下没多久,就“呼噜、呼噜”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,太阳都晒到屁股了,还没有醒来。后来,下尾街人就把“打铁师傅都起来了,你还不起来”,来说教那些睡懒觉的人。“辛苦做,快乐吃”下尾街环境得天独厚,这条街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。尤其是吃的,海里的,山上的,都会到这里来。人们从古田、屏南、周宁、寿宁挑来山货,换回这里的海鲜、咸货回去。在下尾街,可以说,你想吃什么,就有什么。
所以下尾街几乎家家都吃得比较讲究。在下尾街,有一句口头话,叫“辛苦做,快乐吃”,这些生意人、手艺人很辛苦,几乎是从早上眼睛睁开到晚上睡觉,都不曾停歇过,他们都说,这样没日没夜地干,就是为了一个“吃”字。
有一家灯店老板,吃东西很挑剔。早上一餐,比较随便。中午和晚上,他们家的饭桌上总是摆满了丰富的菜肴。其中没有壳石类的海鲜是不能过关的。那些蟳、龙虾、虾蛄,是现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上等货。宁德的海鲜远近闻名,但随着近年对湿地滩涂的破坏,许多 的品种已经岌岌可危了
老板常说,没有吃好,那能干活!他家个个吃得身强体壮。灯笼生意也是他们家做 。他们不仅做宁德本地的活,罗源、连江、霞浦、甚至福州的客商到他们家订货,他们都能保质保量按时发货。
每月的月初和月中,是海鲜集中上市的日子。这几天,下尾街整条街几乎成了海鲜市场。渔民们大鱼、小鱼一路摆过去,都是刚下船的, 的新鲜。我家小门对着大海,大门临街,买海鲜十分便利。我奶奶常对着来我家做客的城里亲戚炫耀,我们家是把锅烧红了,到街上买鱼来煮还来得及。今天的宁德东湖市场就坐落在曾经下尾埠头,下尾街与它相连的地方热闹如往昔那时候,我家里不时有杀鲎。鲎都是两只,一公一母合着卖的。公的个头大,母的个头比较小。杀鲎的时候,把鲎尾巴绑在柱子上,下方放一个盘子,把鲎的肚皮朝上,用刀沿着它壳的四周软肉慢慢地割下来,这样,鲎的血就会流入盘子。鲎的血是兰色的,把它和鲎肉合在一起煮,味道非常鲜美。鲎肉加上几个鸡蛋,搅均匀后,放在锅里煎,香气四溢,很好下饭。鲎壳可以做瓢子,舀水用,可以卖钱。现在比较少见鲎了,偶尔在市场上看见有一、两碗鲎肉在卖,不知是否正宗,有无染色造假。
不管多忙碌,也要吃好每一餐,是下尾街人的共识。鲎抱蛋在今天也是一道名菜阿彬家的棺材店和他父亲的“水烟筒”小时候,我有好几个在一起玩的小伙伴,家里都干着不一样的行当。阿彬家开的是一间棺材店。大大小小的棺材摆满了他家的大店铺。
他家的后院很宽敞,后院再出去,就是滩塗。这滩塗涨湖的时候,和外面的大海连在一起,很多捕鱼的船,跑运输的船来回穿梭;海水退去后,就是一片海泥,就是所说的滩塗了。滩塗也不平静,有跳鱼、有蟹、有时还能见到章鱼。
我们小伙伴们经常从他家里出去,在滩塗上抓跳鱼、抓蟹。跳鱼很好捉,跳鱼看见有人来,就纷纷往洞里逃。我们把手往它的洞口插进去,手掌觉得有东西动的时候,连泥土一起往外拔,准能逮到两、三只跳鱼。捉蟹就不一样了,蟹是横着走的,我们只要瞅准,断它的退路,也很容易捉到。
阿彬的父亲很亲善,他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孩子。
他抽“烟筒”烟。“烟筒”就是用铜制作的一种抽烟工具。把水烟放在烟筒头上,烟筒头下是一下铜管,铜管插在盛着清水的烟筒座上,在烟管座的另一侧又插进一条弯弯的铜管,用“纸媒”吹着火后,点上烟筒头上的水烟,人的嘴巴则含着那一根弯弯的铜管悠闲地吸着。听说经过烟筒座清水后的烟吸进人体,不会“热”,不会上火。
“纸煤”是一种导火的纸筒,它是用粗纸卷成的,大约30公分长,筷子大小的纸圈。那时候,火柴还十分稀少。老人们在空闲时,就会坐在那里搓“纸媒”,搓好的“纸媒”就放在一个竹筒里,就象现在人们把笔插在笔筒里一样。那时家里都烧灶,三餐烧火完了后,就把柴灰盖在火红的炭上,这样的炭火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不会熄灭。人们要取火时,就把“纸媒”伸进灶里,只要“纸媒”碰到炭火冒烟时,就把它取出来,用嘴巴对着冒烟的“纸媒”慢慢地吹,不一会儿,“纸煤”就冒出火来了。有一天,阿彬的父亲要到里屋洗烟筒,他的烟筒每隔一些时候都要清洗、换水,他叫我们几个小孩子帮他看一下店铺。虽然店铺里摆满了棺材,但我们已经都习惯了,并不害怕。
不一会儿,街上走来了一位中年人,他走到店门口时,停了下来,对着店里的棺材,这里看看,那里瞧瞧。同伴小飞历来嘴快,只见他跑到那人的跟前,问道:“叔叔,买棺材?”那人愣了一下,马上沉下脸,朝小飞狠狠地瞪了一眼,很生气地走了。
事后,我们把这事告诉了阿彬他爸。他爸笑着说:“这事如果是大人去问,那人非摔你巴掌不可。原来,大凡经过棺材店的人,大都有想看看棺材怎样,又有一点惧怕的心理,他们在店门口躲躲躲闪闪,想马上离开又要多看几眼。这样的人,不是买棺材的人,这时,我们千万不能问人家是不是要买棺材,否则有些人会感到很晦气,会很生气的。只有在客人走进店铺认真挑选的时候,我们才能够和人家谈生意。“挂门搭”与“臭瓜袋”我的另一个小伙伴叫阿棋,家离街比较远,沿街没有店面。阿棋的父亲做鱼货生意,是挑着担子,走街窜巷叫卖的。在他的鱼货担里,主要是咸鱼、虾干之类。有时,顾客需要什么鱼,要他捎上,他会很热心地服务。到了农历四、五月份,是*瓜鱼、白鱱鱼大量上市的时候,他就把担里的咸货换成 鲜的*瓜鱼、白鱱鱼送到城里去贩卖。
那时候,没有冰箱冷冻,如果担里的鲜鱼卖不完,自家又吃不了,他就会把这些鲜货“掛门搭”。所谓“掛门搭”就是卖主选择几家老客户,事先没有告知,把少量的鲜货(一般两、三斤)包装好,掛在人家大门的门扣上,货款则由受货人家随时随意给。这些人家不会刻薄辛苦叫卖的小贩,一般都会在一、两天后,按市价足额付款的。阿棋的父亲说,解放前,这样的“掛门搭”比较经常,解放后,就逐渐少了。现在,有的小贩在傍晚后,把货担里的余货直接挑到人家的家门口,或者进到屋里,把货物硬摊给人家,钱则由买家有钱的时候给。这样的“赊货”,也叫“掛门搭”。
当然不是所有的货都可以“掛门搭”的,有些鱼不新鲜了,甚至变味了,是决不能“掛门搭”的。这些鱼拿回家后,就要马上腌制起来。他们的家里放了好几个大木楻,都是用来腌鱼的。木楻里放了浓度很高的盐水,把鱼放进去,就不腐不烂。有的*瓜鱼放进去,时间久了,会发生很浓的臭味,人叫“臭瓜袋”。“臭瓜袋”闻起来很臭,可是把它蒸熟了,吃起来却是很香的。现在人们崇拜湖南的臭豆腐,很喜欢吃它。我们下尾街的“臭瓜袋”,如果将它开发起来,把它包装起来,说不定比湖南的臭豆腐更负盛名呢!话虽这样说,城关人是很少买“臭瓜袋”的,因为它名声不好。可它却是古田、屏南来的客人的 货,一则因为它便宜,二则因为它长途拔涉不变味。
很多小鱼小虾,卖不完的,也都往木楻里倒,腌起来。
经过一段时间后,木楻里的盐水要更换。这更换出来的盐水又叫盐卤,闻时有一股臭味,看时有*色冒泡,但它却是可以卖钱的。
我奶奶经常去他家买这种盐卤,一般一次买一、两桶回家,大约有40多斤重。买来的盐卤放到锅里,慢火熬煮,同时在盐卤里放一大块生姜,有的还放桔皮。经过一整天的熬煮后,锅里盐卤的大部份水份会蒸发掉,剩下的液体会变得粘稠,气味会很香的,这就是上等的“鱼露”了,这样的鱼露好吃,还可以下饭。如果能得到马鲛鱼、海蛎、虫念肉腌制的盐卤,那熬出的鱼露,咸中带甜,就更鲜美了。我的奶奶我奶奶是一个很正统的宁德妇女。她说,满清末年,从下尾街码头上岸的福州船上的人讲,外面闹革命很利害,有的男人把辫子剪了,有的妇女不緾脚了。奶奶说,她本来对緾脚很反感,从八岁开始就在緾脚,那是很痛的。现在听说外面有人不緾脚,她也偷偷地不緾了。但是还是要做样子给家里人看的,要不,会被往死里打的。我们仔细看看奶奶的那双脚,不长不短,是半途不緾脚的缘故。我的一个姨奶奶,就不一样了,她的脚真是“三寸金莲”。她虽然比我奶奶小两岁,奶奶说,她很守规拒,所以才有那样的脚。
奶奶的娘家在南门,邻里姐妹们天天聚在一起裱锡箔,裱好的锡箔要挑到下尾街来卖,所以她小时候也常来下尾街。她去下尾街卖箔的时候,见过我爷爷,他很会做生意。我奶奶说,有一天,我爷爷被人带着到她家里来“相亲”,那一天,她和众姐妹们也正在家里裱锡箔。奶奶喜欢做生意的人,所以后来就嫁到下尾街来了。
早上才四点多,我奶奶房间里就有动静了。那是奶奶起来抽烟“吧嗒、吧嗒”的声音。从我记事起,奶奶就会抽烟。她也抽“水烟筒”。每当空闲的时候,她就会搓很多的“纸媒”放那里,备着抽烟用。奶奶起床后,其他人也要陆续起来了。奶奶不让人早上起床后多话,也不喜欢小孩子早上哭闹。言多必失,孩子哭闹影响大家做事,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一家人一天的情绪,进而影响一天的生意,一天的收入。这些事,奶奶很在意。奶奶要大家早起、早睡,她常说,“家兴吃早饭,家败吃早瞑”,意思是,兴旺的家庭,早早地就吃早饭了,衰败的家庭早早就吃晚饭了。奶奶的这些教诲,至今仍然深深地扎在我的脑海中。
不是只有我们家早晨早起,下尾街整条街的人都是这样。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尤其是五十年代,五都下、福宁下(下尾街人叫霞浦一带叫福宁下)的农民会用船到城关来舀粪,买来的粪水用船载回去。卖粪是下尾街妇女的一项经济来源。买粪的人会沿街吆喝“舀粪、舀粪”,女人们听到后,会马上跑去给自家的粪缸里加水,把粪兑成稀稀的,然后叫舀粪的人来看粪给价,双方讨价还价是非常激烈的,最终都会以每担粪一毛五到两毛钱结价。有的人家,一家才五、六口人,常常是前天才把粪舀出去,今天又有粪卖了。我奶奶非常反对这种事,她常说,种田人和我们做手艺、做生意人一样,都要靠血汗赚钱,都要对得起良心。我们家的粪从来不兑水,一两个月才卖一次。五月五赛龙舟奶奶特别注重逢年过节。
五月初五是端午节。我们家在初三就开始包粽子了。初五这天,奶奶和母亲就专职司候家里的事。我们小孩子早上就换上新的短衣短裤,每个人胸前还有一个用五色线编制的网兜,网兜里放一个染红的熟鸡蛋。有的人家的小孩,胸前还掛臭丸,也是用网兜装的。到中午的时候,家里人还会给孩子的耳朵、脸上捈雄*,那雄*是用*酒调制的。
我家对面有一个地方,叫船厂,从我知道这个地方起,就没见过它有造过船。想是在早先,这里就是个造船的地方。船厂的面前是大海,船厂是龙舟比赛的起点,我们常常是早早地就到这个地方,等着龙舟比赛开始。中午要吃饭,要捈雄*的时候,奶奶总是到这里来找我们,准能找到。龙舟比赛很激烈,常常是几十条船对垒,抢 。这时,锣鼓喧天,船上人叫号声此起彼伏。岸上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助威呐喊,一派热闹的景象。龙舟赛结束后,人们会集中很多船,往海里抛粽子。说是送给海龙王的。现在的东门兜农行、闽东大广场一带,以前有叫“马厝坪”、“马厝坪灰炉”的,这些地方前面就是海,人们往这一带的海里抛下的粽子特别多。这一带常发生小孩子溺水的事情,人们要海龙王保佑各家孩子平安成长。“做七月半”和“请路头”七月十五中元节,下尾街人叫“做七月半”,也不一定都是在七月十五日这天烧纸祭祖。各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。有的兄弟多的,已分家的,祭祖则各家依次分数日进行,说是让祖宗分开几天吃,若同在一天祭,会让祖宗忙不过来。现在的下尾街人仍然延续了上辈人留下的这一规矩。
但是,有一件事情却是被现在的人省去了,那就是“请路头”。
什么叫“请路头”?按我奶奶的说法,每年农历七月,阎王都会给所有的*灵放假,让他们回到阔别已久的 去游荡。我们祭祖,那是请回有主的*灵。还有许多无主的小*,它们到 后,没有吃的,没有钱花,要去乞讨。七月三十日,阎王要将它们收回去了,人们就在这天晚上12点前,备干果、年糕等斋品,还有纸钱,在自家门口,路口,有桥的,在桥上,祭奠它们。它们吃了斋,拿了钱, 还要送它们“草鞋仔”,让它们路上好走。它们到了阎王那里,会替 说好话,让人们和谐平安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,“请路头”在下尾街很兴盛。
“草鞋仔”,现在下尾街还有卖。就是用稻草编制的小小的草鞋。以前都是南门一带的妇女在编制,现在南门的田都盖房子了,没有了稻草,南门也不出“草鞋仔”了。现在下尾街卖的“草鞋仔”,都来自蓬峰三村的山上,山上还有一些田可种,有稻草,妇女们空闲时,编制些这东西,挑到城关来卖。
七月尾下尾街“请路头”,可乐坏了乞丐。各家各户摆在路边的干果和糕等斋品,都不会再收回家。每年的这时候,下尾街的乞丐特别多,他们专等着这一餐。现在,有时能听到下尾街上年纪的人讲“七月尾*仔夺斋”,来比喻东西被许多人哄抢,这话里“*仔”,实际上是指乞丐。“我饼比月饼圆”中秋节快到的时候,我父亲就会到饼店定做月饼。过去的月饼很圆,比十五的月亮还圆;很大,比十五的月亮还大。用尺量,直径可能有30公分。月饼做的很薄,馅是单一的红糖。饼的正面撒了很多黑白芝麻,还贴上一张彩画,画着嫦娥奔月,天宫玉兔,猴子水中捞月等。小孩见了很喜欢。
八月十五这天晚上,孩子们拿了小竹椅,坐在院子前,等着月亮升起来。月亮慢慢地升起来了,他们就会拿起月饼,对着月亮,不断地摇晃,嘴里唱着奶奶教给的儿歌——“月啊月,快来着,你饼大还是我饼大,你饼圆还是我饼圆。我饼比月饼大,我饼比月饼圆”。这样的赏月过程,下尾街人叫“显月”,“显”有显耀的意思,显示 的东西比你天上的还要好。最忙是年尾农历十一月下旬以后,下尾街就渐渐地繁忙起来,每天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汇集到这里来,他们有的来贩货,更多的人是来购买年货。
“做香”店,是最忙的店铺之一。下尾街 的做香店,至少也有五家。做成一柱香,从头到尾,都要靠睛天。所以这些店铺应付年底的大买潮,都是有所准备的。
春天,他们派伙计去乡下四处收购“香末”。“香末”是一种香味清淡的树皮磨成的粉末。以前的里占、三望农村有人专门加工出售。这样的树皮比较少,把它磨成粉,一担一担地出售,是费工费时的事,所以要买香末,都不是卖家送上门来,而是买家上门去定购。买来的香末,再加竹签、香精和粘合物,要在夏天把一柱一柱香制出来。这几家的房子都很挤,没有空坪,他们都在自家的房顶上开辟出一个晒台,下尾街人叫“毫头”,把做好半成品香整齐地排在竹丙上,再拿到晒台上曝晒。晒干的香,一大捆、一大捆地用粗纸紧紧地包起来,防止回潮和香气溢光。做香的人,平时生意平淡,只有在年底,才会大赚一把。
除了香店,下尾街还有两家烛店,做烛店铺里放了各种各样的模具,先把烛芯扣在一个模具的中央,把融化了的烛油倒进去,冷却后,就是成型的腊烛了。他们的店铺,年底也很繁忙。
题联店也很忙碌,年底了,搬家的,结婚的、祝寿的,人们都要题红联祝贺。
打金店、打银店、打锡店、打铁店、刺绣店、元宝店、篾料店,陶器店、理发店、水产店、南北干货店、灯店、法师僧择日馆,……下尾街几乎所有的店铺在年底都在忙,整条街不知是人淹没在街里了,还是街被人潮淹没了。只有两种店不能讲忙,一是药店,一是棺材店。那时,福安人开的元昌号药店,店的后门直通下尾街。这两种店铺讲忙,人们就遭殃了。“长岁饭”、“涝伙饭”和“压火种”经过整整一个多月的忙碌,下尾街的人直到除夕这天,才算稍微平静下来。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,店铺的卫生要做,店门板要洗,有的人还要忙家里的卫生。店里有雇伙计的,店主要忙着结账,付钱,让忙了一年的伙计们回家过好年。有的店铺老板要在年底追回现金账。外面的生意事看是完结了,里面要做的事还真不少。
年三十下午2点多,祭祖完成后,母亲就开始准备年夜饭。年夜饭在下尾街,又叫“长岁饭”。
“长岁饭”很丰盛,除了平时常吃的蟳、虾,新鲜鱼类外,还有鸡肉、鸭肉、羊肉等上桌。我父亲用猪网油当皮,用香菇、瘦肉、姜、葱、香油等做馅的“鸡卷”,油炸后,又香又脆,回味无穷,我们特别爱吃。桌上还放了自家酿的红酒,那是大人们喝的。“长岁饭”的桌子上,每年摆出的筷子,总要多一双,奶奶说,这是寓意添丁。有一年,我的大叔在上府(下尾街人把南平、建欧一带叫“上府”,把霞浦叫“福宁府”)进货,赶不回来过年,奶奶在“长岁饭”的桌上,也摆了大叔的一份饭,一双筷子。
“长岁饭”上,奶奶还会宣佈,吃了“长岁饭”就是过年了。过年全家人不能说不吉利的话,凡事都要说“好”,要“好”字当头。面前的饭、菜不能都吃光,要留着明年吃,要年年有余。这些话,奶奶年年都说,我们年年都听,而且还装着很认真听,因为讲完这些话,大人们就要给小孩子们发压岁钱了。
吃罢“长岁饭”,小孩子们就玩去了。大人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母亲开始“涝伙饭”,这是下尾街每家在年夜饭后都要做的一件事。先把水放到锅烧成七、八成热,然后把洗干净的米放到锅里,再把锅烧开,用笊篱把米捞上来,放进蒸笼里。这时米还只是半熟,到明天要吃时,把蒸笼放到锅里蒸,这样能较快把饭蒸熟。这么做,也包含连年有余的意思,把今年的饭留到明年吃,这过一夜就是第二年了,多吉利。
忙完了这件事,再洗一遍锅灶,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摆设整齐,把地扫干净,在蒸笼里、米缸里、所有放东西的容器里都放两个红灿灿的桔子,把店铺里的大称、小称的头尾两端,用红纸扎上,预意明年生意红火。对联和灯笼下午已经贴了、挂了,再检查一遍是否满意,还要为全家人整理好明天早上要穿的新衣服,还要烧热汤招呼小孩子们洗澡……
年夜要压火种。就是把灶膛里的火炭用草木灰盖紧,这样,火炭不容易熄灭,第二天早上(大年初一)拨开草木灰,就可以延续火种了。正月里大年初一,下尾街各家各户不串门,大家都在自家的屋子里,一家人尽享一年难得的这一天的大团圆、轻松的日子。
初二早上开始走亲访友。人们大都是喝完这家的酒,又到那家喝酒。他们要把过去一年的辛苦尽抛脑后,用酒来燃起更美好的憧憬,去迎接新的一年的更大收获。
祝寿是下尾街过年的一个主题。人到五十岁,就要做寿了。亲戚邻里有五十、六十、七十的,大家都要去祝寿。所谓祝寿,就是煮上一碗线面,面上放些海蛎、豆腐、香菇之类的菜肴,再在碗边对称方向各放一个无馅肉丸,也有人放剥了壳的熟鸡蛋。做寿人家收下这碗面蛋后,就会回礼两个红包糕。红包糕是用红纸包裹着的米糕。只有5公分×3公分见方,1公分厚,小小的。那时是回谢人家好意的主要礼物。也有人用红桔子回礼的,那时红桔子比较少,用的人也不多。
正月初五是“开假”日,这一天,下尾街所有的门店都陆续开张了,鞭炮声此起彼伏,人们希望通过这喜庆的气氛,迎来新的一年的好彩头。老二家偷偷摸摸的婚礼下尾街也有衰落的时候,那是年以后的事了。大跃进、大食堂,年的大饥荒,下尾街的许多店铺都关闭了。繁华的街景变得萧条了。
物资极度匮乏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。
下尾街原来有几家理发店,后来理发师傅都被集中到大街上一个叫“大众食堂”的地方理发了。
有一个叫老二的理发师傅,是古田人,他十几岁就到宁德学理发,后来出师了,在下尾街租了房子,娶妻生子。年,他的大儿子结婚。老二提前几天通知邻里街坊。没有发请帖,市场上买不到写请帖的红纸,也没有墨水,更没有人敢写。
到了这一天,晚是八点了,大家才陆续到老二家,请的人不多,最多也只有两、三桌、没有酒桌,是用木板支撑起来当桌子。上桌后,每位客人都会自觉地从自己的衣袋里拿出筷子,汤匙和小杯子,摆在桌子上。那年头,自备餐具赴宴已成规拒。
没有放鞭炮,一是买不到那东西,二是也不敢燃放。客人差不多到齐后,婚家还要把前后门拴紧,生怕被人发现。一旦被人举报,就会有专业的人士来驱散聚集在这里的人们,主人还免不了要受处罚。没有酒,用汽水代酒,那时,县食品厂里有散装的汽水买,主人会提前几天,一天买来一些,偷偷地囤积起来,顶酒用。没有行婚礼,没有猜拳,简单的几道菜后,这宴席就结束了。各人收起自己所带的用具,一个个分散地溜回自己的家去。私制香烟的小伙伴们年前后,香烟很紧张。香烟是凭票供应的,水烟不要票,而且便宜,很多人都抽水烟。但抽水烟很麻烦,要备许多工具。那时,市场上有烟纸类,有的人用烟纸裹上水烟抽,也有人卷这样的香烟出卖赚钱。
我们几个小伙伴商量,何不也弄卷烟出卖呢。于是我们偷偷地跑到搞卷烟人的家里去看,这卷烟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。回来后,我们就动手做起来,经过几天的试验,我们终于摸索出一套生产流程,做出的香烟还供不应求呢。但做香烟的原料却来之不易。
那时,下尾街有许多霞浦、罗源的人乘船来往,他们时常带一些烟叶到下尾街偷偷地出售。知道他们的交易地点后,我们也到那里买来烟叶。把烟叶切成丝状后,拿去晒。晒好的烟叶要加上麻油,再加进旧的烟丝,放在簸箕里搓,搓到软棉棉状了,才能用。
旧烟丝是我们捡烟蒂得来的。要捡到很多烟蒂也不容易,我们最常去的就是人民会场的垃圾堆。人民会场的垃圾堆在大门里面,管大门的人叫“祖仁”,他经常来下尾街,和我们父辈有交往,我们知道,他们都是好朋友。
“祖仁”伯伯知道我们这些下尾街的小孩子,也知道我们捡烟蒂是为了什么。所以每次我们到人民会场,只要他看见,他都会开门让我们进去,我们每次都能捡到很多烟蒂。
做卷烟的工具很简单。用木板订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,盒子的边壁上挖两道槽,两根筷子一样的圆竹子穿进槽里,把烟纸放在盒子底部,一支筷子压住烟纸,并沾上少量的浆糊,在纸上均匀地放上烟丝,两只手握住筷子的两端,慢慢地把烟丝裹进纸里,然后往上卷,上面的一支筷子是起到压住烟纸另一头的作用,当烟纸卷到上一根筷子时,稍微压一下,使浆糊和纸接触紧,向下一拉,一支香烟就做成了。那时,我们人小手灵,一人一天能卷好几百支香烟。老木制卷烟器做好的香烟,我们分头拿去卖。我们的生意很好,几天一结算,每个人都能分到一、两块钱。
那几年,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,我们给供销社放牛,每天每人可以赚2角钱,我们去洋尾码头卸煤炭,中午饭带去吃,一天有3角多。还到金涵苗圃拔过草,到北山农场锄花生草,每天都能赚到一些钱。那些年,我们这帮下尾街的孩子们,都才十四、十五岁。尾声下尾街直到年改革开放后,才又恢复了生机。现在下尾街的西半边已经被菊地商场、福海市场开发,东半边街也已残缺不全,但是下尾街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多大改变。很多东西,而今也只有在下尾街才能买到。宁德人“去下尾街买东西”的口头禅,现在还在说。
下尾街的房子可以倒塌,下尾街也可能不复存在,但是下尾街的人和事,以及下尾街人的传统精神,已烙在我的脑海,长久不会消失。·End·
责任编辑丨何巧银
值班主任丨林翠慧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