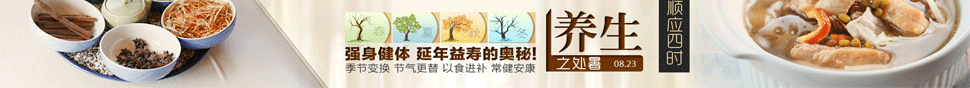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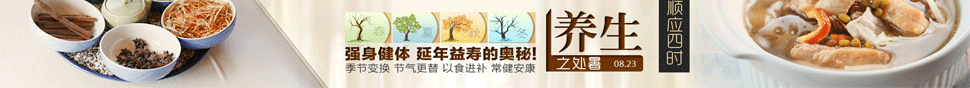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我老家的田野里,最多的就是稻子,为主粮。西瓜、油菜,花生、棉花,以及豆类和薯类,在乡亲们心目中似乎都是配角。这样,作为重点培养对象——稻子,理所当然,都长势喜人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,紫蓬山南部地区,田里一年可栽种两季水稻。那时的秋冬季节,金光闪闪的早稻堆放在农家,金光闪闪的晚稻铺盖在田野,真是一片稻子的海洋。评判家里是否富裕,不看房子和车子,就是看稻子。门口的大草堆是最大的骄傲。儿子长大了要找对象,不说家里钱多,也不夸儿子多能干,家里的稻子就是“B超检查”,结果一目了然。
的确,稻子是乡亲们勤劳和智慧的结晶。那时,“双抢”时节的割稻和栽秧,简直就是一场场鏖战。立秋前半个月,天气就开始了疯狂地炎热,中午的田里表面的水温有四十多度,头顶上的太阳*花花的。而有太阳的日子正好是割稻子的*金时刻,农人们争分夺秒地把成熟的稻子割断,铺晒在稻茬上。太热,想来点雨凉快一下吗?不,下雨会把稻子淋湿了,越热越好。吃苦耐劳的乡亲们,面朝*土背朝天,挥汗如雨,右手握紧镰刀,左手划一道弧线,一把攥住四五组稻棵子,右手伸刀再划一道弧线,用力一拉,嚓啦一声响,一束沉甸甸的稻把子就收入掌心。就这样,在火炉般的田野里,身影起起伏伏,稻枝摇摇曳曳,镰刀闪闪烁烁,一片又一片稻子被乡亲们用手工割倒,在似火的骄阳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。
插秧活计的技术含量要高一些。在割稻子和插秧之间,有一个活计叫使牛,也叫犁田打耙。就是赶着水牛,把一个满是稻茬的田块,通过翻土、破碎、耙平等工序,整理成一个漠漠水田。由于水牛怕热,这些工作必须在晚上完成,那叫真正的披星戴月。插秧开始了。一田的秧把子,像绿色的鸭子在水田里漂摇。人一跳下田,拿秧把、解秧草、分秧苗、插进泥,都是在瞬间完成的。随着双腿的向后移动,随着均匀的手与水轻击的啪啪声响,面前刹那间绿茵茵一片,棵棵秧苗排列整齐,组织有序。是诗是画是歌,全凭你的感觉——反正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。但是,没有亲自体验过,是无法知道田水和汗水对接了多少次的,也领悟不了苍蝇和蚊子困扰人的那种滋味。
晚稻成熟季节总是让人心潮澎湃。霜降之后,晚稻子熟了,故乡的田野充满意趣。经过夏的冶炼,秋的滋润,田野稻田的颜色趋向翠*,在目力所及的视野里连成了一幅以丰收为主题的国画。秋风送爽,稻浪千重,那稻的波涛随着江淮丘陵错落有致地飘舞着,在我故乡的田野上尽情展现辉煌灿烂的色彩,点染着天空,村庄和河川。稻穗饱满,每一粒稻子都像金子一样实沉。撸一把过来,搓一搓,吹去稻糠,内里的米晶莹如玉,异常光洁,散发着新米的香甜。
如今都机械化了。我记不住手工割稻、使牛、栽秧的活计何时消失了,但那情景总是铭刻在心上。那天回老家,站在潜南干渠河堤上,远远地对着一幅金*的稻田发愣:它和我们的“介”字型的老房子一样,成了故乡的风向标,成了我心中永恒的动力。
(作者:鹿伦琼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合肥八一学校)
转载请注明来源《民族时报》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