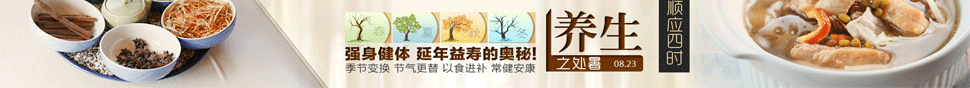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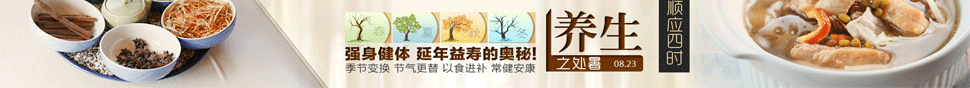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○劳动中的下放知青(资料图片)
○郭贤芬当年的招工表
○招工进城后的郭贤芬
○当年的宣传队员几十年后重聚下放的大队
○下放时的郭贤芬
从年12月22日下放,到年7月6日回城走向新的工作岗位,她经历了近三年的知青生活。虽然这几年的知青生活有欢乐,有艰辛,也有遗憾,可以说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都经历过,但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青春岁月,因为是那片土地养育了她、锻炼了她,使她知道农民的艰辛,懂得做人道理,学会自立自强……
下放第一站:宣传队
年12月22日,冬至。也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因为这一天,我从合肥市来到了肥西县义兴公社席井大队郭南生产队,开始了近三年的下放知青生活。而年2月2日出生的我,那一年还没满17周岁。
我到农村报到的当天,郭南生产队的队长就告诉我,大队宣传队刚成立,要选人参加,我看你正合适,明天就让他们送你去大队报到吧。我没想到的是,我下放的第一站竟然是大队宣传队。
年的冬天特别冷。我到宣传队时正是下大雪天,我岁数小、人也不高,而且面*肌瘦。宣传队的导演于爱华是位非常漂亮的知青姐姐,她当时正准备导演《白毛女》片段,见到我后第一眼就说我最适合演喜儿。
我们排练的地点是三间空房,土墙、泥地,也不知是谁家的。虽然排练比较辛苦,甚至期间没水喝,但我们个个都很投入,认真地听导演指挥。知青们都很聪明,点到即领会。比如导演说,“一定要哭得伤心,撕心裂肺地哭喊。”当我演到“喜儿”看到爹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时,情不自禁地一下扑到爹爹身上,拼命揉着爹爹“撕心裂肺”地哭喊着,“死也不进*家门……”被演狗腿子的张广新等人从“爹爹”身边拖走。
正当我们排练起劲时,有一天有位知青的母亲(也是我家的街坊)从合肥来宣传队看排练节目,回到市内跟邻居说:“郭家五丫头在人家男孩身上揉来揉去……”不好听的话传到我母亲耳里,母亲听到这话很生气,但她相信我。春节回到家,母亲就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就一五一十地和母亲说了是宣传队排节目。要知道,当时我到宣传队时间不长,互相都还不认识、不熟悉,我甚至不知道是谁演的“爹爹”。
我们是席井大队的第一届宣传队,队员基本都是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,当然也有当地的社员和一些在校学生。这些人都能歌善舞,而且能写能编、自导自演,当时正赶上喜迎“九大”召开。宣传队的任务当然结合形势编排节目。
我们经常下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宣传演出,当然,我们也和淝河汽车制造厂的宣传队搞汇演,在一起交流经验、互相学习。但我们能隐隐感觉到淝河汽车制造厂的宣传队看不起我们。这也难怪,因为那么大的单位,能进宣传队的又都是佼佼者,他们认为一群农民还能和他们比?但他们错了,他们没想到这样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宣传队是非常棒的。
记得我们两家第一次汇演是在淝河汽车制造厂的大礼堂。那天汇演的第一个节目,就是我们大队宣传队演的,是副队长的笛子伴奏、知青陈恩华的独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演出结束赢得场内一片叫好声;紧接着就是舞蹈《满怀激情迎九大》,并且由知青刘贤树吹笛子、孔德权和梁华祝两把二胡伴奏,舞蹈当然也不逊色。演出当中也穿插着对方的节目,最后,我们又跳了一支舞蹈《献给亲人解放*》,我是第一个跳转着上场的。那次汇演非常成功,大家都很高兴,也让淝河汽车制造厂的宣传队对我们刮目相看。
一心一意学干农活
知识青年下放农村,最主要的事当然是和农民一起干农活了。
那时农村肥田基本上用的都是绿肥、农家肥,春季要积肥打秧草。提起打秧草真够苦的,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镰刀怎么用,割草时必须一手抓草一手用镰刀砍草,开始我不敢,社员庆芬手把手地示范教我。慢慢地自己感觉会了,但是想双手动作协调一致还比较难。
我记得,第一天打秧草就不小心把左手食指砍得肉翻过来,我也很勇敢,用嘴一吮,把破处复位,回到家大嫂撕块火柴盒上的皮,搞块旧布用线给我包扎好,就这样也没发炎,来回几次包扎,手好了但留下刀疤,几十年过去了,这美丽的刀疤永远留在我的食指上。
春耕生产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农活——拔秧。拔秧看似容易,但是真不好学。记得第一次下田拔秧时,我看着社员那熟练的动作,一会工夫一个秧把捆好甩到田边。我也学着拔,但是大部分秧都断了,简直是糟蹋。后来我仔细观察,发现他们的双手摆平往前推着拔。慢慢地我也能拔了。但是捆秧把还不行,一不注意全散了,甭想甩到田边,我认真向他们请教,
终于像模像样能过关了。但是一上午下来我的衣服上下全是泥水,简直就是个“泥人”。经过这样几天的艰苦劳动,虽然到了晚上真是腰酸背痛腿抽筋,但总算是学会了拔秧。
说来你可能不信,因为我刚下放农村时没看见农民点麦子的情景,到了春天雪化了,看到大片的农田里长着绿绿的植物,因为在城里没见过,一开始我竟然不知道那是麦苗。几个月一过,青青麦穗出来了,真是麦浪滚滚,长势喜人。渐渐地,麦子成熟了,要开镰收割了。
收割麦子,对我来说又是一道难题了。首先割麦子的刀是长长的,而麦秆比较滑,一开始我根本用不好,几次手指被刀砍,往往是老伤没好新伤又出现,但我有种韧性,每次都是包扎止血后,带伤劳动绝不退缩。但是麦子收割好,捆成把又成了一道难题,其他社员捆的麦把都很漂亮,而我不仅半天才捆一个把子,而且形状就像驴打滚,一点不好看。不过好在这些我都挺下来熬过去了,学会了割麦子。
最终,我学会了栽秧、施肥、割稻等一系列的农活。
农村处处皆学问
我下放生产队的土地是半岗半圩的,因此田亩紧张,麦子割了的田地,很快就有两个男社员驾两条老牛犁地。地翻好了、放水、踩秧草、绿肥下地,过不了一程就要栽秧了。栽秧之前队长安排我们女社员把田的四周杂草割掉,这时候是要光脚下到泥田里,而我最怕的就是蚂蟥。但是我不能退缩,就学着他们的样子下了田。我看见他们从田边拔些绿叶往腿上揉,于是我也如法炮制。后来我才听说那草叫“辣鸟”,蚂蟥怕它。看来处处皆学问啊。
除了蚂蟥,田旁边还有我最害怕的蛇。只要见到蛇,我会吓得连滚带爬,泥水会溅大半身,小姐妹们不但不解围,反而笑得更欢畅了,一些调皮的小姐妹有时还有意趁我不注意用蛇吓我,有一次往我衣服口袋里装条蛇,我吓哭了,她们才说,“水蛇咬个包,到家就要消;赤板蛇咬个洞,到晚就要送(即死的意思)。这是水蛇,你别怕。”她们讲得轻松,但我还是很害怕。看着我“狼狈”的样子,她们高兴极了。不过这也让我终于知道了水蛇和*蛇之分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,和大部分农村一样,我们生产队翻田地基本靠牛犁田和人工挖田拐。我记得当时生产队有三间牛棚两条老牛。我刚到农村时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,有次到牛棚去玩,看到社员用草绕子包*豆喂牛,就想牛怎么还吃*豆呀。后来社员告诉我,那是因为老牛生了小牛犊,要加强营养,要尽快让牛身体健壮起来,因为春天要靠它耕地。有时社员们还叫我试着喂牛,但我怎么也不敢。不过我从此后知道了晒干的牛粪可以用来分给社员烧锅。
年底分红,我分得了三十多元钱,回城里时我全部交给了母亲。母亲非常开心,我也很高兴。因为我觉得不仅自己能养活自己了,而且还能为家里解忧,自信感大增。
我的日常生活
当年我们下放农村,国家只供应半年口粮。很快下放就满半年了,我即将要自立门户,生产队也已给我选好房址,准备早稻一收割就把我房子盖起来。
终于到了盖房子的日子。我记得那天一早,生产队长就安排十多位青壮年社员来帮忙干活。他们有的从半里路外的田里挑来土砖,有的和泥,还有的当瓦工砌墙。很快,新房就盖好了。那时房子也很简单:一个双扇门,一个小木窗,还是没有窗门就几根窗衬的那种;房内则锅碗瓢盆和水缸、水桶等一应俱全。铁锅是前两天从集上买的,其他东西如水缸、水桶、桌子、床和铁锹等都是从市内母亲那用板车拉来的,而这其中有不少东西还是外婆当年使用过的。
因为刚开火烧饭,我生怕误工,所以每天早早起床。正常情况下,我早早起床后先把早饭的粥烧开,用锅灶里的余火把稀饭闷熟。早上起床后,我通常还要把屋内卫生打扫一遍,一听到上工打铃声时,我就把梳子装口袋里,一路小跑去听队长安排工作,这时我顺便把辫子梳好。这样的话,社员们下班有饭吃,我也能吃上饭,
记得有一天,我看天有点亮了,就赶紧起床,拎着小水桶和淘米篮子,到生产队最好的水塘去拎水、淘米、洗头。到了水塘后,我首先拎一桶水放塘埂上,把米淘好,再走到水塘中间把头洗好,然后拎着那桶水回到家就烧早饭。早饭也烧好了,但奇怪的是怎么还听不到上工的铃声呢。我又回到床上睡了一觉,这时上工铃声才响了。后来我仔细想了想,肯定是我把月色当天亮了。
慢慢地,我也成了一名地道的社员了。我跟社员们学会了很多农事和日常生活杂事。而且,我后来还去公社大礼堂参加了卫生员培训报告会。医院院长到义兴公社传授赤脚医生“一根银针、一把草”知识。那时各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室,各生产队都培训卫生员。我们生产队推荐我去公社、大队学习,最初我们跟医生学习,他教我们认识中草药和药用性能、学打针、换药等知识,有时他带我们去挖中草药,我学得很认真,也为我后来我从事的医务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我回城啦
我很感谢下放在肥西义兴公社席井大队郭南生产队的那段生活,因为它让我得到了锻炼,使我学会了很多知识。我和社员们打成一片,关系很融洽。不过就在我干得起劲的时候,传来了一个消息:知识青年可以回城了。
经过一番等待的煎熬,我终于拿到了一个招工指标。年3月12日,我填了招工表。又经过一番考核等,我终于在年7月6日招工进了省公路工程管理处工作。
从年12月22日下放,到年7月6日回城走向新的工作岗位,我经历了近三年的知青生活。虽然结束了知青生涯,虽然我的知青生涯有欢乐,有艰辛,也有遗憾,可以说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都经历过,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青春岁月,因为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、锻炼了我,使我知道农民的艰辛,懂得做人道理,学会自立自强……
那段知青岁月,永远永远值得怀念!
□郭贤芬/口述程堂义/整理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