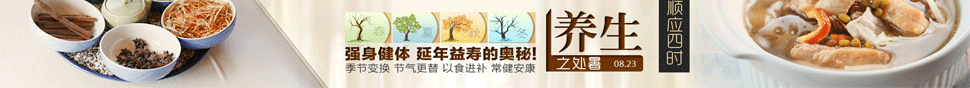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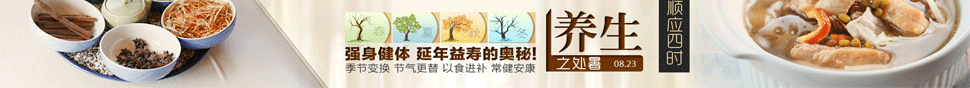
“冬至大如年”,苏州人吃冬至夜饭,搭吃年夜饭一样,饭镬里也要放一把荸荠,盛饭时,每人碗里都要有两个,吃到了,叫掘着元宝哉,寄寓着财源滚滚。因为荸荠也叫马蹄,从前有一种“马蹄金”,正好与荸荠的模样、名称碰拢在一堆。
故而,荸荠在苏州人眼里一直是招财之物,据说清朝乾隆十五年(),一家姓沈的人家建屋开店,开挖地基时挖到块形色都像荸荠的石头,据此就把店名题作“野荸荠”,经营茶食糖果,还有野味,兴旺了毛两百年,直到年歇业。现在浙江的国、省两级 “野荸荠”就是当时苏州开过去的分店。
荸荠种在浅水田里,苏州种荸荠,正月留种,春分时将荸荠成行密排田中,不多时,就抽出了草茎,极细而中空,内有白节,如同一丛丛席草相仿。到了小暑脚边,分种定植,耘耥诸事与种稻一样。历经一夏,地下匍匐茎的顶端膨大成块茎,生成荸荠,直到冬至前后,撅起来上市,一直吃到春天。
“天津鸭梨儿不敌苏州大荸荠”,苏州出的荸荠是“苏州荠”,自从明朝以来名望普普,集中产于葑门外,尤以车坊出的鼎鼎好,叫卖者必称“车坊荸荠”,爽脆清甜,生津解热,细腻得吃口没有一点点渣滓留在嘴里,远销京津。北京人吃了,觉着算得嫩的天津鸭梨跟它比比,还推板一点点,欢喜得不得了,清末之际,北京“凡公宴,加笾中,必有此品”,以致于市面上的荸荠“一枚须 文”。而且这还是色黑个大,品质稍次的品种,如果另外一种“红嫩而甘”者被北京人吃着,不晓得要如何着迷哉。
苏州的荸荠有红、黑两种,红的细嫩、品质好,只是比黑的个头小、不耐储运,故而那时运到北方去的基本都是“带泥可以致远”的黑荸荠,因为个头大,也叫“虎口荸荠”,据说拇指和食指张开,只能放一个。
苏州人吃荸荠,生熟皆宜。生吃,要把皮预先扦掉,叫“扦光荸荠”,店家卖起来,串在竹签子上,10个一串,累累白玉,味并雪藕。只不过,一定要把顶芽扦干净,否则有感染姜片虫的可能。还有一种吃法,把荸荠放在竹篮里,挂在通风处,过点日脚就成为了“风干荸荠”,皱皮捺搭,别有一番风味。
熟吃,当小吃,清水煮熟,称为“焐熟荸荠”,冬、春午后,热吹浦烫的吃格十数个,惬意得极。吃剩下来的荸荠汤也有用处,小朋友出了痧子,以前总要天天喝一碗,因为荸荠清热益气。烧小菜,一般把荸荠切成片,搭仔荠菜,放点肉丝清炒,也是鲜美爽隽,有个名字叫“炒双荠”。
苏州人把荸荠叫作“葧(be)脐”,明正德《姑苏志》里就是这么称呼的。葧脐这个名字来自“鼻脐”的谐音。荸荠,扁扁圆圆,顶上突出一个灰白色的芽,模样蛮像凸出的肚脐,最早的名字叫“鼻脐”,“鼻”就是凸出隆起的意思。后来依着读音,各地派生出葧脐、荸荠……一串别名,读书人还叫它“佛脐”。荸荠一词,始见于北宋时期的《本草衍义》,现代蔬菜学认为荸荠两字既可显示这种植物是草本的特性,又能传意“鼻脐”的古意,故而最终成为了正式名字。
明王磐《野菜谱》里的野荸荠插图
荸荠非但好吃,而且漂亮,皮壳颜色黑里泛红,稳重而宁静,有一种漆色就叫“荸荠漆”,髹了这种漆的家具,富贵大气又不失温馨。除此之外,荸荠还有两样有趣的用处。一是它的草茎可当听声音的玩具,民国时的《洞庭东山物产考》说,“以指爪掐茎,往上捋之,成五音六律之声”,而且可以反复使用,不会破断。二是据说荸荠与铜会发生反应,如果把荸荠储存在铜器中,铜器就要坏掉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。
文:俚人图:来自网络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